名師雲講堂 回顧 NO.18 | 張鴻聲:城市文學研究的曆程
發布日期:
2020-05-08
作者:
浏覽次數:
212
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關于中國現當代城市文學的研究漸成熱點,而城市文學研究是如何凸顯出來、又經曆了怎樣的演變呢?張鴻聲教授首先在現代文學史總體視野中從三個方面辯證地考察了這一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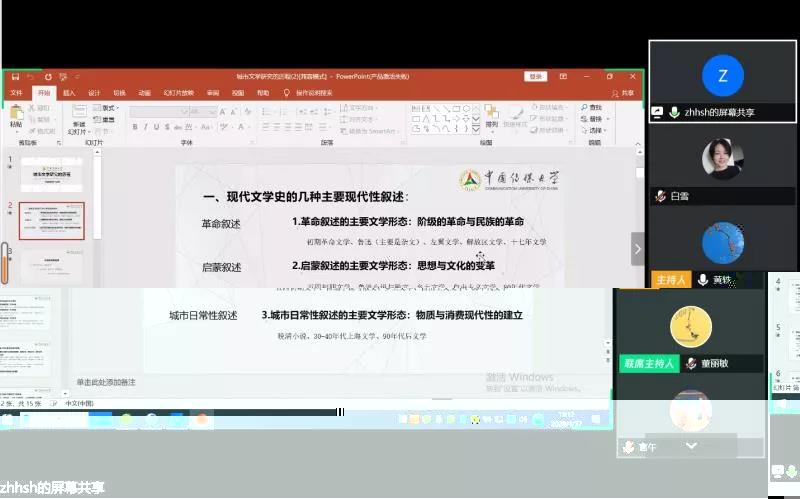
一是文學史中的城市文學叙述。他概括了現代文學史的幾種主要現代性叙述,包括“革命叙述”、“啟蒙叙述”、“城市日常叙述”,詳細地闡釋了不同叙述中的主要文學形态,并對幾種叙述的演進做了曆史分期說明。他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以重點涵括初期革命文學、魯迅及其雜文、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十七年文學為主構成了“革命叙述”的文學史;從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思想和文化的變革,五四初期文學、魯迅小說與散文、鄉土文學、自由主義文學、“80年代文學”等成為研究的重點,由是發生了從“革命叙述”到“啟蒙叙述”的文學史轉變;而90年代後,又出現了建立在物質與消費現代性上的城市日常性叙述,具體體現為“晚清文學”、“30~40年代的上海文學”、90年代後文學等成為研究熱點。在這三種文學史叙述的曆程中,城市文學經曆了從無到有、從有到盛的過程。
通過對新時期以來城市文學研究的曆程與動态進行梳理,張教授認為,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大緻經曆了作家作品論——流派論——形态論——文學史論——新的近代史史觀等各個階段,有日漸超出傳統城市文學題材、流派、形态研究範圍的迹象。通過對海外漢學家理查德·利罕、張英進、李歐梵、王德威,國内學者陳平原、趙希方等人的城市文學研究著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人們的關注點,從“文學表現城市形态”開始轉移至“文學對城市性的表達”,甚至是基于城市性表達而來的曆史觀念,而這一現象預示着我們已經不能固守傳統的城市文學研究了。張教授将這種新的城市文學研究範式指稱為“文學中的城市”研究,并且從文學文本通過想象和虛構“賦予城市什麼意義”、“為什麼賦予這些意義”、“是怎麼賦予城市意義的”等三個邏輯性問題,對這種新的研究範式突破傳統反映論走向話語論的内在結構進行了深刻的闡釋。
講座最後,董麗敏教授對張教授的講授予以回應。董教授認為:張教授從學術史角度清晰而又系統地勾勒了“城市文學”研究範式發生發展的過程,以此拓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城市研究的新空間,給人以很大的啟發,主要有這三點:其一,張教授展現了當前城市文學研究從“城市文學”向“文學中的城市”的研究重心的轉化,這意味着“城市文學”研究不僅僅局限在文學領域内部,而是具有了跨學科研究特性,需要引入曆史、理論、社會學等多種學術資源建構起更為完整的知識結構,才能撐得起這一轉化;其二,張教授強調了“城市文學”研究從反映論向話語論的轉化,這打破了僅僅在寫實的維度上來定位文學之于城市研究的作用,凸顯了文學所獨有的理解和打開城市研究的方式其實更在于賦予城市以人文意義,這一認知,極大地提升了文學研究在整個城市研究中的價值;其三,張教授很好地處理了“大叙述”(現代性)與“小叙述”(本地性)之間的辯證關系,超越了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使得對于上海這樣的“摩登城市”的解讀更接地氣。
張鴻聲教授多年來專注于城市文學和城市文化研究,此次講座既高屋建瓴又詳盡入微,學理闡釋深入淺出、精彩疊起,參會者均受益匪淺。
撰稿:楊高強